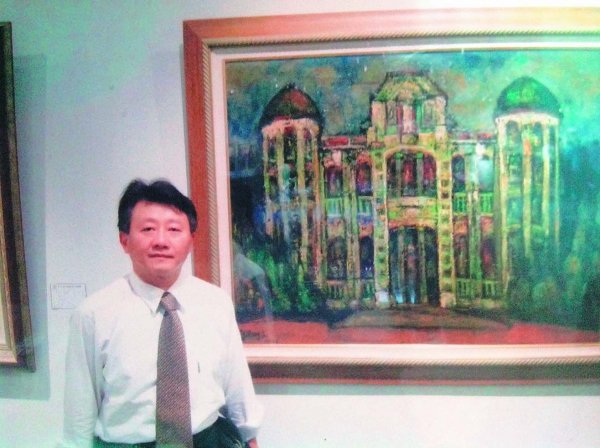然而,分析蘇奕榮的作品則不容易從時間發展的順序中看到明顯的風格變化,也就說,他的油畫風格無論從主題、內容、表現形式,都無法從時間的前後順序裡找到他們相互延續或變化的脈絡。因此,要解析蘇奕榮的油畫作品,必須先釐清蘇奕榮在創作上的一個特性,從這個特質中才容易使觀察者較深入地了解他的作品。
如果以時間軸線為基準,分析蘇奕榮自2007年至2010年的油畫風格和題材、主題等內容,我們會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困境。主要原因是,他並非以單一主題、單一題材、單一視覺意象,循著時間的推移,發展自己的繪畫風格。因此,我將轉換成以表現主題、題材和視覺意象等相互併行的觀察方式來解析他的作品與創作的脈絡;這樣則更容易讓觀眾理解他這個階段的全貌。
從現有的資料上看,蘇奕榮2008年赴德國慕尼黑民俗博物館進行官方性質的文化交流和成為台灣南部重要美術館體「南美會」顧問,是他1971年師從臺灣本土前輩油畫家沈哲哉先生習畫,經歷將近四十年時間在油畫創作上的重要累積。也表明他在油畫創作上逐漸穩固基礎並且取得成果的過程,旋即在2009年他便創辦「府城人物畫會」擔任創會會長。而2007年開始密集的油畫創作,恰好也對映著蘇奕榮的文化藝術活動開展,發揮自己的行動力與實踐力,這兩種人格特質也反映在他的創作之上。
我們需要先拋開「時間順序」的因素,暫時不再當做蘇奕榮創作的參考座標,而先將視線集中在他的油畫題材上。風景、靜物、人物等三大類是他的選擇主要表現題材。風景有分為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兩種類型;靜物以花瓶為主;人物則以女士、裸女等女性題材為大宗。進一步根據前述三大題材的表現形式而論,風景題材從結構性的探索到色塊與筆觸、肌理的表現,呈現他在繪畫空間問題上的觀點。靜物為單純地體現量和色彩的單純化(我將忽略這較少部分的的分析)。無論就數量和質量而言,人物題材無疑是蘇奕榮最感興趣的一部份,從表現手法的更加多樣也看出他的強烈企圖。
為使對蘇奕榮有較深入的了解,就以蘇奕榮最感興趣,也最具表現力的人物化為主要對象進行分析。蘇奕榮的女性題材多數以寫實手法營造抒情、浪漫的氣氛,表現女性婉約溫柔的氣質,無論是裸女或者衣著各異的女性,蘇奕榮在圖面背景處理上發揮更大的想像力,有時候讓人物懸浮在一個讓人迷惑的空間裡,使觀者有更大的自我解讀空間。我認為,蘇奕榮表現人體的柔軟和安適,表現女人恬適神情與優雅姿態特質的同時,他在背景處理的手法變換,重新賦予整體作品不單純是人物題材的模糊性,也成功地讓女性題材產生「弦外之音」的效果,例如,2010年作的(曲線)、2009年作的(嬌怯),以及2007年所作的(嫣紅)。
值得一提的,蘇奕榮除了以具象寫實的手法表現出女性的溫柔婉約感受,他也嘗試用現代藝術的表現手法,放棄對空間、人物形象的描繪,轉為以色彩、線條和人物整體造型互為一體的表現一種象徵意味的主題;例如,2007年作的(秋思)雨2008年作的(夏日)。這樣的興趣同樣出現在他的風景題材作品之中,而蘇奕榮對於這類抽象與象徵意味的表現手法,會不驚異地在不同題材作品中轉換出現。
有幾件看似無法歸類再蘇奕榮三種題材之中的作品也需要近一步說明它們的意涵。2008年作的(耀色)、(蛻變),以及2009年作的(餘)、(你你我我)等這幾件結構性很強的作品,擺脫了蘇奕榮表現手法的主流,轉向另一種新的視覺意象。經過簡化的圖像已經幾乎讓人無法分辨它們的輪廓所代表的物象,抽象式的繪畫語言直接指向了一個大環境或者人與事、物相關的象徵內容。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觀眾需要很長的時間去思考畫面傳達的意義內涵,也可以用很短的時間在耀眼的色彩、流動力強的線條相互的結構中獲得視覺上的滿足。
2009年蘇奕榮作的(密碼)讓我們走進一個迷宮裡,破壞的物理空間和滿是鏡子反應與反射的圖像,依稀可以辨識的魚、水果和風景更增添這記作品的神秘感。如果,蘇奕榮擅長用自己的眼光詮釋他自己鎖定的對象,那麼這件作品則是他對自己一段時間裡發生過的各種瑣碎事件的紀錄。
從上述的分析鍾,約略可以知道位何無法在時間的順序中去理解蘇奕榮的創作風格關係。他的表現手法不因為題材而受限制,他的創作想像也不因為時間而中斷或徹底改變;他會在不同的時間裡不斷探討同樣的主題,他也會在同一時間裡對完全不同的主題感到興趣。
我雖然從未與蘇奕榮謀面,但從他的作品多面向表現裡,似乎在隱約間也看到蘇奕榮具有對自身週遭事物「好奇」、「好動」、「愛玩」的性格;當然,這也是他在油畫創作上的重要動力。僅從三年的創作歷程裡簡略分析,並不能很透徹地將蘇奕榮的油畫創作內容做出完善的說明,但這三年的作品確實顯現豐富的面貌和他現階段創作的重心所在。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依照蘇奕榮的性格特質,很有可能再下一個階段,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出現,而我們也期待看到他更多、更新的創作。